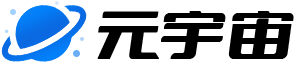金價上漲的秘密:美元主導的世界貨幣格局正在巨變
作者:歐陽曉紅
 制度如何讓交易更順滑
制度如何讓交易更順滑
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落地上海、跨境二維碼統一網關上線試運行、CIPS將迎來十周年,這些看似零散的舉措,如果連成線,就會發現中國正在構建一種“交易驅動型的人民幣基礎設施體系”。
這不是我們在說“來用人民幣,”而是說,“你們想交易嗎?人民幣會越來越好用的。”
跨境人民幣業務,由此從過去的“政策引導”階段,邁入了“基礎設施支撐+市場自主選擇”階段。IMI調查顯示,外資企業的人民幣結算使用率從2024年第三季度的40%升至第四季度的67%。這一躍升,尤其在歐美澳企業中,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基于純粹的商業理性:流動性增強、清算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和制度環境日益友好。
2025年9月24日,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在上海正式啟動,數字人民幣跨境數字支付平臺、數字人民幣Blockchain服務平臺及數字資產平臺等三大業務平臺同步亮相。該運營中心旨在成為連接境內外金融基礎設施的橋梁,推動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向規模化、合規化與智能化演進。
據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陸磊介紹,數字化時代貨幣和支付體系的升級演進是歷史的必然。中國人民銀行致力于為改善全球跨境支付體系提供開放、包容和創新的解決方案,提出的“無損、合規和互通”三原則已成為法定Crypto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本準則,目前已初步構建數字人民幣跨境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同時,探索有利于提升監管效率和穿透性的資產數字化創新,增強結算透明度和價值流轉智能化程度。業務平臺落地上海,不僅是便利跨境支付的具體措施,也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建設高度契合。未來,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支持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行穩致遠,為跨境貿易與投融資便利化提供堅實助力。
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吳偉表示,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及業務平臺落地上海,將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注入強勁動力。上海各相關部門要充分依托業務平臺,不斷拓展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擴大使用范圍,助力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
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打通了由制度預期到市場聯通的通道,三大業務平臺的落地意味著,從技術底層到應用層都在為人民幣國際化、資產化做準備。同時,該運營中心強化人民幣生態的“數字中臺”角色,為未來跨境數字人民幣交易、鏈上清算、資產撮合提供制度支撐。此外,該運營中心也在制度層面預埋了“未來場景的接口”——確保人民幣既能于傳統銀行間系統高效流轉,亦能在未來的鏈上資產世界中無縫調用。
在涂永紅看來,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正式運營及三大業務平臺同步推出背后的核心邏輯在于:用國家信用做支撐,比私人穩定幣更可靠,避免了幣值波動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同時保留了Crypto的便利性。而上海的平臺把發行、流通和清算全鏈條打通,還能兼容現有系統,支持智能合約,既高效又可控。在Crypto領域打造一個更安全、有公信力的“中國方案”,尤其上海作為金融中心,這一步可能對跨境支付和全球規則制定都有影響。
政策協同也在同步推進。國家網信辦于9月13日發布的《促進和規范電子單證應用規定(征求意見稿)》中,明確鼓勵在貿易、物流、金融領域使用電子單證,并支持金融機構在合規前提下探索數字人民幣等新型跨境支付方式。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信號:人民幣國際化,不再依靠政策宣示,而是力圖通過交易體驗贏得市場的選擇。人民幣的選擇
數字人民幣跨境基礎設施的搭建不是為了取代誰,而是為了讓我們“能在不被切斷的系統里,自主完成交易”。
這也解釋了為何數字人民幣國際化原則是:無損、合規、互通。它不是對抗性的制度設計,而是兼容性的技術演進。在交易雙方看來,人民幣能否被持續選用,取決于其作為交易媒介的綜合競爭力——包括流動性充裕度、資產安全性、制度透明度與技術支持能力。
當然,這一進程必然伴隨挑戰。正如IMI問卷調查所揭示的:超過60%的企業認為跨境人民幣政策復雜且更新頻繁,近50%的企業將“資本流動障礙”視為主要瓶頸。這些現實阻力,無疑增加了企業的合規成本與操作顧慮,降低了市場使用的“體感溫度”。
為化解這些“冷點”,未來需要在三個層面重點攻堅:
疏通“血管”:通過政策簡化與流程優化,減少不必要的資本流動限制,提升資金循環效率;
打造“盾牌”:重點發展在岸衍生品市場,提供豐富、高效的風險對沖工具,為境外主體持有人民幣資產保駕護航;
精準“滴灌”:設計更具適配性的金融產品與服務,助力民營企業將使用意愿轉化為實際行動,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微觀基礎。
涂永紅提出,應構建“人民幣+Crypto”的雙輪驅動模式。借助數字人民幣在成本、效率和透明度上的優勢,將其深度嵌入跨境貿易場景,同時提升金融機構的跨境服務能力,激勵企業將人民幣全面納入其現金管理、資產配置與風險對沖的戰略框架。
這一切的努力,都指向一個清晰的愿景:推動人民幣從當前國際市場中的“可選”資產,逐步進階為在全球貿易、融資與儲備中“不得不持、不得不用”的硬通貨。這一轉變無法一蹴而就,它需要的是深刻的金融改革、堅實的基礎設施、豐富的資產體系、廣泛的國際協作以及有效的風險管控——所有這些支柱必須協同推進,方能支撐起一個真正國際化的貨幣體系。
當人民幣的使用最終超越行政引導,依靠交易網絡自身的力量實現自然擴展,它所建立的信用,才將是真正堅實而可感的全球信用。
我們今日所見的種種跡象——從“企業的主動選用”到“北向資金的持續流入”,從“黃金的歷史高位”到“美元權威的溫和消解”,并非彼此孤立的事件。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的全球貨幣環境。
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出的貨幣持有“三種動機”——交易、預防與投機,其本質正是揭示了市場參與者如何依據風險偏好與未來預期,感知并響應貨幣的“溫度”。溫度升高,意味著信心恢復,資金從靜止轉向流動,從觀望走向參與;溫度降低,則預示著避險情緒主導,流動性被“窖藏”,市場進入保守狀態。
這些現象,正是同一場宏大浪潮激起的不同浪花。
如果歷史的敘事曾長期由掌握信用與清算體系的國家書寫,那么今天,人民幣正站在參與重塑下一章歷史的起點之上——不是以顛覆者的姿態,而是以交易撮合者、金融創新者與規則共建者的身份。
有溫度的貨幣,終將回歸交易本身,并在每一次選擇中,定義未來的信用。